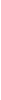房玄龄忙完了政务,回到家中。
刚一进门,便见一人恭敬的候在院里。
“崇义?”
房玄龄愣了下,似乎没想到对方会在自己家中。
旁边,管家房成赶忙上前解释:“老爷,李大郎早就到了,老夫人做主,让他进来等着……”
“嗯,老夫知道了。”
房玄龄摆了摆手,打发房成离去。
四下无人,李崇义这才整了整衣袍,躬身行礼:
“今日早朝,多谢房相出手。”
“贤侄莫要多礼。”房玄龄伸手将其搀起,说道:“老夫只是就事论事,弹劾侯君集一事,与你父无关。”
李崇义抬起头,眼圈泛红:
“我知道,房伯不想承认,可我却不能装作不知。”
“魏公、刘侍郎,还有朝中诸多御史……这么多人站出来弹劾侯君集,定是得了您的允许。”
“所谓患难见真情。”
“我父被侯君集逼着喝酒喝死,放眼整个朝堂,也只有您肯仗义出手!”
“大恩大德,崇义不敢相忘!”
说着,便要下跪行大礼。
“贤侄不可!”
房玄龄急忙一把拉住他。
停顿了一下,随即低声说道:“其实,老夫今日出手,也是顺势而为。”
“哦?”李崇义愣了下:“您这是何意?”
房玄龄未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贤侄可知,当初李药师灭了东突厥,回到长安后都做了什么?”
李崇义马上道:“主动告病辞官。”
“嗯,那他灭了吐谷浑后,又是怎样做的?”
“再次辞官,闭门谢客……”
“那现在,你再看侯君集呢?”
李崇义浑身一震:“您的意思是……”
“都是圣意啊!”
房玄龄轻叹道:“侯君集征服高昌,自大膨胀,天子这是借着我们的手,在打压他啊。”
李崇义直接瞪大眼睛:“这么说,侯君集入狱…仅仅是敲打而已?”
“所以,莫看这次弹劾声势浩大,实则根本扳不倒他。”房玄龄说着,回首望向太极宫方向,目光深邃:
“因为陛下,还不想让他死。”
听着房玄龄的解释,李崇义整个人僵在原地。
他本以为,这次侯君集定会受到重罚,却未想到自己白高兴了一场。
沉默了片刻。
他闷声问道:“既然如此,房伯为何依然选择了出手?”
“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房玄龄收回目光,看着他说道:
“这世上本就有许多难事,也有诸多难以跨过的鸿沟。”
“面对此般情况,便要放平心态,凡事不可强求,却也可何事都不做。”
“故而,吾等只需做到六个字便可——尽人事,听天命!”
“呼……”
李崇义深吸一口气,神色渐渐恢复如常,拱手道:
“不管如何,小侄还是要多谢房相大义。”
“嗯。”
房玄龄沉吟了一下,说道:“你这次挑头攻击侯君集,太子等人必然不喜,需立刻跳出这个漩涡。”
李崇义一愣:“还请房伯教我。”
“长安大丧之后,你便回老家守孝……这是唐律,亦是百善之首,谁都挑不出什么。”
房玄龄说着,眯了眯眼睛:“待三年孝期过后,你再出现在世人面前,届时,一切皆会风平浪静。”
“好!都听房伯的!”李崇义重重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浓浓的不甘:
“侯君集如此猖狂,莫非真的拿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房玄龄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听老夫一言,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记住一个字——等!”
……
“等?就这么简单?”
凄厉的北风吹过,将裴行俭惊讶的声音传的老远。
他瞪大眼睛,盯着身旁的房赢,身上的戎装,被风吹的紧贴在胯下的马背上。
“裴兄,小点声儿.....”
房赢下意识的回首望了一眼。
两丈之后,数千飞火军,正静静的端坐在马背上,队首的“唐”字大旗迎风飘展。
“我有一事不解....”
陈阿宾与房赢并肩而立,俊秀的脸上,一如既往的冰冷:
“河间郡王乃皇室宗亲,当今陛下的堂兄,这样尊贵的身份,莫非还比不上侯君集一个外臣?”
“你还别说,真比不上……”
房赢摇了摇头,给阿宾政治科普:
“李孝恭虽是皇室血脉,但出道之时,却是随着高祖打天下的。”
“早在武德三年,便被封为‘赵郡王’,武德六年,更是坐上了尚书左仆射的位置,爵位、权利皆来自高祖……所以严格意义上说,他是高祖的人。”
“侯君集却不同。”
“这个家伙,可是参加过玄武门之变的。”
房赢贴近陈阿宾,低声问道:“如果你的当今陛下,你会选择偏袒谁呢?”
嘴里热气吹到脖颈,陈阿宾的脸蛋红了一下……
她端坐在马背上,强自镇定道:“可根据坊间传闻,那场惊变中并没有侯君集的影子。”
“呵呵,你也说了,那只是传闻。”
房赢轻笑一声,反问道:“若他什么都没做,为何会成为玄武门五功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