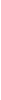千里之外的西北边城,萧璟立在明宁跟前,面色沉冷听着她的话语。
他并未立时答复应允,明宁心下慌乱,拉着他衣袖的力道,愈发的急切。
几瞬后,萧璟拂落了明宁紧攥着他衣袖的手。
他这样的动作一出,明宁脸色彻底惨白,一旁的杜成若跟着松了口气。
下一瞬,萧璟启唇说的话,却让两人的反应,翻了个面。
萧璟目光没看明宁,而是看向了军帐外头,漠北的方向。
话音沉冷,吩咐道:“传信回京告知母后,郡主和亲异族,受辱多年,而今归朝,理当厚待,让母后,在京中宗庙的玉碟里侧妃的位置,写上郡主的名字。”
玉碟之上写了名字,可不明摆着,是要将回朝的明宁立做侧妃。
明宁送了口气,暗道不枉自己费尽心机筹谋算计。
杜成若则在萧璟话落后,面色微变。
玉碟,至于萧璟,可比大婚要来的意义更重。
不久前在长安的那场大婚,之于他,不过是演一场戏,应付皇后,也瞒过朝臣。
所以,萧璟是不曾在玉碟上写她的名字的。
玉碟上不曾落笔,来日尘埃落定,他身登帝位,她回返西北,青史御笔都能抹去这场做戏的婚事。
百年之后,谁会记得一场没有留下丝毫证据的婚事。
可一旦写在玉碟之上,就再也抹不去了。
杜成若压根不准备日后入宫,更不可能留在萧璟身边,其实他让谁做侧妃,日后史书工笔同谁并肩,都和她毫不相关。
君主的宠爱给谁,哪有做臣下多嘴的资格。
可杜成若,即便心知自己无权置喙,还是难免暗骂世道不公。
真正救他的云乔,被他欺负成那样,冒名顶替的杜成若,却活得这样畅快。
凭什么啊。
她隐隐有股冲动,想要当初的真相告知萧璟。
却也知道此时绝对不能多嘴。
罢了,左右云乔已经离开。
何况,萧璟这些年来,青梅竹马护着长大的,就是明宁,而非云乔。
他和云乔,也不过是这一年里,短暂的一段露水情缘罢了。
瞧着他眼下对明宁如何,再想一想他那时待云乔又是如何。
杜成若想,当初究竟是谁救了他,也许早就不重要了。
她自个儿沉在思绪里时,听得萧璟交代明宁道:“孤初到西北,军政繁忙,抽不出空陪你,眼下便要去寻杜将军议事,你好生养伤,有什么事,让护卫去寻杜成若即可。”
萧璟语毕,跟着便出了军帐,去见杜成若的父亲,询问如今两军局势。
杜成若原本也该跟着前去,此时却特意落后了半步。
她瞧着萧璟出了军帐后,自个儿噙着笑,走近床榻,撩开明宁的床榻,手猛地碰了明宁方才仍在渗血的一道伤处。
她没用力,只是做出这般姿态而已,明宁还是吓的花容失色。
眼瞧着明宁畏惧的样子,杜成若唇角笑意更冷。
紧贴着她,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在她耳边警告道:“明宁,好自为之。别以为从前你做的事,就没有旁人知晓。既然得偿所愿就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再被我发现你的狐狸尾巴,我可未必会看在你死去的父亲面上,再饶你一次。”
明宁白着脸,装的无辜,声音怯怯道:“你……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杜成若懒得和她多费口舌,也不再言语,径直起身也出了军帐。
另一边,萧璟已然抵达杜仪帐中。
太子大婚匆忙,杜仪又了解自己的女儿,自然不难猜出,那场在京城的婚事,只是一场戏,便只是如从前一般相处。
两人端坐军帐,聊起军务。
杜仪并不知晓萧璟记忆模糊,也自然不似京城的人,早得了皇后吩咐。
萧璟记忆模糊,许多事都记得不大清晰,这才急着寻杜仪询问,好让自己心中有底。
西北缺粮缺银,他原本想到的最坏的结果,是他抵达西北,便得知军队哗变。
也做好了若是军队哗变,要如何应对。
这些年来,皇帝根本不想给西北半点银钱。
早年间,西北的军饷尚能支撑,连年的军费开支,几乎拖垮了西北,自萧璟自少年时离开西北,许多年里一直是他和皇后掏着自己的府库贴补西北。
在他眼里,这收不上税银,送不了美人的大漠,只有孤烟和长河落日,又无半点值钱的玩意,被漠北夺了就夺了,没什么好在意的。
全然不会想,今日失了西北,来日便失河套,祁连山也从此不保。
之后,一旦中原生乱,北方的胡族,就能长驱直入饮马黄河。
他只在意他做皇帝这一世的快活,哪管数十年过去,他死后的洪水滔天,和后人百姓如何。
可萧璟到底和皇帝不一样。
萧璟少年时便在西北疆场撒过热血,最知道这茫茫大漠之下,是多少中原将士的尸骨。
西北淌着的血,说不准,都比此地的水要流得急切。
几代人,守了数百年的国土,哪里能弃。
军帐外风声烈烈,军帐内静寂肃穆。
萧璟亲自给杜仪倒了盏茶,奉到他跟前。
声音恳求至诚,由衷道:“数年不见,将军风采依旧,大敌当前,萧璟以茶代酒,多谢老将军这些年来苦守西北。”
杜仪顿了下,瞧着眼前的萧璟,不由的想起许多年前,萧璟还是个小少年时的模样。
那时他还不知晓他是皇子身份,只以为是个寻常送来参军的京中破落贵族家的膏粱子弟。
也是,寻常人家,但凡还有富贵出路,哪会送家中尚未及冠的孩子从军。
更何况,是皇族出身的皇子呢。
皇后舍得将膝下独子送来西北,也是走的最对的一步棋。
不是西北的血色,养不出后来长安城里杀伐果决的储君。
许多年过去,前些时日,听闻他在江南强夺了个人妇,杜仪也曾想过,少年时英勇无畏一腔热血的萧璟,会不会也成了当今皇帝一样的人。
直到今日再见他亲赴西北,瞧着眼前这个,和少年时相比,更冷寂,更锋锐的他。
杜仪想起当初自己瞧着那人还没长枪高的少年郎,身上累累血痕,倒下又爬起的模样。
意识到他和当今皇上,终究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