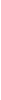好轻,又瘦了!
这是催寄怀抱起萧辞的第一个感受,随后他又忍不住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一个不听话的女人,死了都是活该。
这么一想,催寄怀的脑袋不由浮现房间里,萧辞坐在床头温柔向催时景诉说心事的一面,他心中不由更加不畅。
催寄不做停留,抱起萧辞快速离开小巷。
镇上的人全都在为疫情发愁,有人看到萧辞被袭偷带走,可却没有一人上前阻拦,毕竟在灾难面前活着已经不易,谁又还有心思去管别人的闲事呢。
月上梢头,还未到春天的夜晚格外寒冷。
萧辞昏昏沉沉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
回想起失去意识前发生的事情,她不作停留,想要爬起来,却发现自己双腿软绵绵地使不出力来。
自己这应该是被下药了!
萧辞脸色更白,费尽全身力气爬起,跌跌撞撞往房间门口走。
她须必有人到来前离开这里。
可惜她的手才碰到门,门就已经被人从外面推开,萧辞被迫后退,无力的脚一软人控制不住的往后倒。
在她就要落地之际,一只有力的大手穿插过她的腰间,将她扶了起来。
萧辞慌忙抬眼,对上的是一双漆黑的眼眸,以及被半截铁面具遮住的脸。
“你是谁?”萧辞警惕质问:“就是你将我抓到的这里?”
“没错,是我!至于我是谁,你不需要知道。”催寄怀故意使用了变音,将身体绵软没有力气的萧辞抱了起来扔回了床上。
萧辞缩在床上,看向催寄怀:“你想要做什么?”
“做什么?”催寄怀冷笑:“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
做了不该做的事?萧辞眨着眼睛,脑子运转,实在是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让人将她掳走。
除非……是那幕后操纵疫情的人。
唯有这种解释了。
她给人治病挡了那人的路。
可到底还是催时景的猜测,也没有怀疑对象,更没有证据,现在说出来只会打草惊蛇。
萧辞抿着唇,想要套催寄怀的话,她刚想张口,就见催寄怀人已经扑过来,伸手将她抓过来压在了身下。
他真的像是在生某种气,对她极尽粗鲁,吻着她的唇粗鲁到像是在咬她,而且他好像对她的双手特别有意见,反复啃咬。
萧辞辱耻欲死,想要反抗可身体使不上劲,根本没有办法用武功,随着携带用来自保的毒药也已经在她昏时被搜走。
萧辞只能哭泣,怒视。
“别这样看着我!”催寄怀占据上位,将萧辞的双手举高至头顶死死扣住,漆黑的眼眸中携带掠夺:“要怪就怪你记不住自己的身份,不该惹的人别惹,这样很难?”
不该惹的人!得到提醒,萧辞脑中灵光闪过,她近段时间只跟催时景有过接触,所以眼前人是因为催时景才对她动了这个手?
想着,萧辞脑中就浮过催寄怀的身影,随即又否定了。
催寄怀已经死了,她可是见过催寄怀血衣的。
暂时摸不着头绪,萧辞只能缩小范围的套话:“你是说催时景吗,他已经离开镇上了,你若是不许我跟他接触,我保证不会跟他再有接触。”
“不是他!”催寄怀早已经捕捉到萧辞的意图,矢口否认,他不可能让萧辞怀疑到他的身上,否则他也不可能会戴面具。
“不是催时景那又是谁,你只要说,我都改,我都听你的。求求你放过我!”萧辞双眼含着泪恳求。
因为方才催寄怀粗鲁对待,她的衣服早已经被撕乱,露出雪白肌肤。
催寄怀也只差最后一步,就能跟萧辞彻底亲密无间。
萧辞实在不想自己再让人一个陌生男人占有,她的身体被催寄怀占有过已经够脏了。
“求求你……”萧辞想着两颗眼泪从眼角滑落,带着哭腔恳求:“只要你不碰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晚了。只有经过这次惩罚,你以后才会记住要跟别的男人保持距离!”催寄怀望着萧辞留下的眼泪,心生不忍,可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没有办法更改。
萧辞更加不能。
他对萧辞只有征服,根本不需要顾及她的感受。
萧辞是他的女人,不听话就理应受到管束!
催寄怀心中烦躁,他不想看到萧辞这双湿漉漉的眼睛,手一扬扯下萧辞一截衣袖绑住了萧辞的眼睛。
看不到眼睛催寄怀心中平和了不少,他不再迟疑狠狠占有,施实着他的惩罚。
压抑的哭声最后变成涰泣,天上的月亮似乎都不忍看到萧辞受苦隐进了云层。
翌日,萧辞满身疲惫地醒来,待思绪回笼,她的脸上露出被辱过后的愤恨,爬起来想找昨晚欺辱她的贼人算账。
等坐起了她才发现,自己身上昨晚被撕破的衣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换,现在的她穿着一袭青色衣裙,衣裙的料子不算好,但干净整洁像是新的。
而她处所的地方也已经不是在那间陌生的房间,而是回到了她在隔离营地,自己的帐篷之中。
怎么会这样?
萧辞恍惚了,这样她不禁生出昨晚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的错觉来。
为了确定倒是真是假,她怀着期待的心情扯开了自己的衣领,当看到裸露在外的皮肤上那一片片暗红色的印记时,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浇灭了她所有期望。
昨晚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萧辞无力又绝望地跌坐在床上,这些时日好不容易焕发出来的生机这一刻枯萎,她再次想到了死。
她的目光落在离床榻不远,圆桌子上的杯子。
只要将杯子敲碎就能得到锋利的瓷片,这样就能割开自己的动脉,让血流出来,彻底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
这般想,就这边行动了。
她从床上爬起来,光脚踩在地面上,昨晚那种身体软绵感已经消失,她伸出手碰到了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