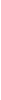回府的路上,任城王又一次思索那几则志怪故事。
尉窈是天子近臣,她通过志怪故事透露的,必是皇帝元恪的决心!尉窈没有捏造虚言,没有制造恐慌,因为任城王对元恪心思的察觉,比尉窈要早。
元恪是君王,却重一己之私,轻社稷臣民,一心想杀保社稷的贤臣元勰。
随着马车时不时的轻轻晃动,任城王在心中一遍遍自语,说服自己必须坚定!
“先帝在时,常以孟子之言告诫诸王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本王忠诚先帝,忠的其实是社稷,图的是经世辟土的大业!”
“我不可犹豫,不可犹豫!我不可胆怯,既然开始做了,就断掉后路,不可胆怯!”
“元勰是我大魏之栋甍,绝不能似比干被冤杀!先帝有弟、还有诸子,我大魏……昏君可以换,栋甍不可失!”
任城王从窗帘缝隙里看夜晚的洛阳城,真是灯火璀璨壮京师,雄心纵横起龙蛇。
八月二十一。
领军将军于烈病重,回光返照难得清醒之际,才知禁卫武官权的变动。
完了,于忠一定做了错事,让陛下失望了!他立即让哭哭啼啼的亲人都散开,只握紧儿郎于忠的手,命令:“你速进宫告诉陛下,就说……诸叔王,都不能留!尽杀!陛下才能真正览政。”
什么?于忠吓地直摇头,以为父亲糊涂了。
于烈急得满脸鼓筋,骂道:“竖子!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天子为什么重用我们于家!于家只忠天子,只忠天……”
攻心火是致命的最后一击,于烈喷出一口血,瞪目气绝。
于忠悲痛万分,尽管惧怕,还是听从父亲的嘱托进宫报丧,他一字不改转述完父亲的遗言,离开宫殿时整个人失魂落魄,瞧见赵芷在殿门口值守,心更加慌。
坏事!赵芷耳力敏锐异于常人,她听没听见刚才他转告给陛下的诛王机密?
疑心一旦种下,只需时机自会如疯草一样滋生。
于烈临终老谋深算,只凭借一句遗言,使尉窈之前算计于宝映、于忠的计策如竹篮打水,算计落空。
于忠是居丧去职了,可是紧接着,皇帝下诏于烈的弟弟于劲升为四征将军之一的征北将军,暂时代禁军统帅职务。
九月初一,高阳王元雍返回京城,皇帝免元雍冀州刺史职,升为司空。元雍也是有准备的,呈上征京畿五万民夫,修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的奏请。
皇帝准许。
初八,皇帝下诏,立于宝映为皇后。
九月下旬,随一道赦免寿春营户为扬州庶民的政令,任城王再次被迫远离朝堂中枢,赴扬州监督淮南军事,只是还没有出司州境,王妃李华颜就因长途颠簸,病情加重。
任城王不敢赶路了,遣人接连急送文书,恳求解除扬州的官职,可恨没等到朝廷的回文,王妃就香消玉殒。
孟太妃亲自给儿媳擦洗换衣,她眼中含泪,话中含恨道:“你辅佐先帝迁都,平定穆泰叛乱,又辛苦推行文教,既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想到皇帝不顾宗族亲情,故意压你的请奏,竟让你妻子病死在路上!”
任城王鼻翼扇动,只掉泪,说不出话。他悔啊!这段时间只顾着筹划这、筹划那,没注意妻子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
元澄似老了十岁,走出帐篷,没想到娇贵了这么多年的妻子,临终是在荒郊野外。
“我以为你能跟我享一辈子福的。”
高祖珍赶紧过来,自认为忠心地提醒:“将军,不能再拖了,这里离洛阳不远,朝廷迟迟不回公文,意思很明显……”
元澄手臂一伸,捏碎高祖珍的喉咙。
皇帝元恪确实是故意不回任城王的辞官奏请,但确实也没料到任城王妃在路上病逝。
有一段时间了,他没让尉窈出谋划策,今晚尉窈来送公文,他只留她在殿内问话。
元恪:“迁都之始,先帝下令鲜卑贵族死于洛阳,必须葬于洛阳。元澄用这条政令为由,再次奏请辞官回京,安葬他的王妃。可是伐梁之征刻不容缓,除了元澄监督淮南军事,朕可以放心,其余宗王里,朕没有好的人选。如何决策?两难。”
尉窈:“孟太妃年事已高,若因王妃病逝伤心伤身,元澄恐怕几年里都去不了扬州了。”
元恪明白,他这次再驳元澄的请求,在朝臣眼中就显刻薄了,而且元澄肯定继续呈奏请,到时随意编造孟太妃因儿媳病逝而伤身,那时还得允许元澄回京。
尉窈继续道:“现在代行扬州军事的是元英,臣遍阅之前扬州的公文,发觉元英好战,几次败绩皆因他过于勇猛、冒失才造成的,但他的优点不能被否认,就是从不畏战。”
“陛下可派稳重的宗室大臣暂时替代元澄,监督元英稳重行事,陛下再从左右侍卫里遣武官同去,以免派去的大臣过于揽权,在该出兵时耽误时机。”
禁卫武官张龙子这时匆匆过来,禀述之事让元恪烦上加烦!才对于家恢复的信心,再次生怒!失望!
皇宫西掖门的东南方向有禁军署,于劲暂代统帅职务,新官上任当然要严格监察纪律。
今晚他来查岗,隔远就听到阵阵污言秽语,等走近了看,只见每个屋舍里都有兵卒在划拳吆喝,盔甲和武器扔在地上,入目乱七八糟!
于劲带着武官来的,可是他不了解禁卫兵的武力,并非队主、队副等武官就强,寻常的精锐兵就弱。
双方打在一起,混战的兵越来越多,直到喧哗声惊到来回巡逻的一队羽林军,这只队伍的武官是张龙子,张龙子担心发生营啸,才赶紧来御前禀报。
营啸是不祥之兆,元恪不敢顾及别的,立即命令赵芷去禁军署控制住哗变。
“杨大眼,你护好陛下!”赵芷奔跑如飞,声随人远,速度实在太快!她下属的侍卫还没集合起来就瞧不见她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