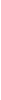逃跑……
不逃跑就是傻子了。
对面人山人海,天上还有个无敌的,王师不打逆风局的。
但问题是大量坦克战车和军车拥挤在桥上,想迅速撤退是不可能,所以很多士兵直接就是拋弃他们的装备逃跑。
而人群中並不缺乏退役士兵。
贼配军嘛!
当兵前就是底层,当兵后为钱卖命,退役后还是底层。
在一个好人家谁当兵的国家,他们也不会得到尊重,再说就他们在外面乾的那些,也的確不值得被尊重。
所以紧接著几个退役士兵就钻进了一辆被拋弃的坦克,其中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標准装弹机,而一个看起来蓬头垢面还是个流浪汉,很明显过去是个车长,他在炮塔上探著身子,熟练的向里面的同伴喊著指令,然后这辆坦克的炮塔稍微转动,炮口昂起,直接对准了前面城市的一座摩天大楼……
“瞄准七楼,害我破產的那家保险公司就在那里!”
他吼道。
里面一台装弹机立刻发出快乐的喊声。
紧接著炮口火焰骤然喷射,震耳欲聋的炮声震撼这座城市,炮口前的气流衝击让前面还在逃跑的士兵们,全都惊愕的转头看著这一幕。
而在同时一二五毫米炮弹在他们头顶带著刺耳的呼啸掠过,几乎瞬间就到达它的目標。
那座大楼的七楼一排玻璃幕墙,在爆炸的烈焰中化作向外喷射的碎块。
“杀光这些狗东西,杀光这些理財经理,保险经纪人,投资顾问,杀光这些银行家,房產商,期货商……”
流浪汉亢奋地吼叫著。
同时操作大口径机枪的他,也瞄准已经变成一个大窟窿的楼层,紧接著子弹的曳光刺出,同样准確打进了距离一点五公里的目標。
一枚枚十二点七毫米子弹就这样消失在那片浓烟的黑色。
他们这狂暴画风让后面的人们也都有点懵,毕竟这样还是有些突然,虽然大家就是要闹事,但上来就是直接开大,还是让人有些猝不及防,不过听他喊出的那些名字,大家又一下子觉得好像就是该这样啊。这一个个名字都代表著底层们的梦想,但同样也是底层们最仇恨的,毕竟在这个国家每一个破產者后面,基本上都有这些人的努力。
谁没被他们坑过?
拒赔率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保险公司。
输不起直接拔网线的期货交易所。
打不过抱团散户直接让交易平台限制交易的证券商。
……
金融资本家和他们的僕从们,靠著各种强取豪夺的手段,把一座座关闭的工厂,一个个破產的家庭变成他们的金碧辉煌。
他们就像一台榨汁机,把小企业主,中產家庭,小农场主们,在这个巨大的机器里挤压,榨出所有財富,用这些財富堆砌他们的纸醉金迷,然后把剩下渣子拋弃,变成街头一个个裹著毯子躺在风雨中的纸箱板上的流浪汉。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所有人都明白这个国家是为什么走到今天,儘管所有人都梦想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他们也清楚这一切。
不然就不会有当年的占领运动。
当年的占领运动换来的是浇水泥沉湖,但今天不一样啊!
他们头顶上金灿灿的天使正在展开双翼,仿佛在用圣光笼罩他们,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考虑那么多?
为什么不能尽情发泄啊!
一个看起来標准的中年社畜,突然走进旁边一辆被拋弃的军车,然后双手握住了自动榴弹发射器的握把,他脸上此刻带著一种异样的红色,仿佛喝多了,但却在用颤抖的双手將这个武器昂起,对准了前面一座带著某著名银行標誌的大楼。
“我还得再还十年的大学贷款,现在就还给你们了!”
他发疯一样嚎叫著。
下一刻自动榴弹发射器开火,伴隨著嗵嗵声,一枚枚四零榴弹以最大仰角飞出。
紧接著那大楼的玻璃幕墙上火光炸开。
“还有我的刚被你们收走的房子!”
他旁边一辆军车上,一个同样的中年男人则站在陶式飞弹旁,在吼声中向著另外一家银行射出飞弹。
……
跟隨杨丰而来的流浪汉,压抑的中年社畜,破產的退役士兵等等,所有知道使用这些武器的,全都像狂欢一样占据那些被拋弃的战车,然后以各种方式向著他们对面那片摩天大楼开火。炮弹呼啸著划破空气,在摩天大楼上炸开,大口径机枪子弹的曳光撞碎玻璃幕墙,甚至这里还有几门被拋弃的迫击炮,几个熟悉的退役士兵站在一二零迫击炮旁边快乐地装填,看著炮弹直衝天空。
而他们后面则是一片欢呼。
前面溃逃的士兵有些惊慌的互相看著,毕竟这要算起来他们责任重大,要不是他们遗弃武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打的可不是几座大楼,而是这个国家真正统治者的脸啊!
这些是真有能力决定他们命运的,一旦老爷们秋后算帐,他们这些都跑不了的。
除非他们能反击夺回这些武器。
但是……
“轰!”
天空中一声巨响。
他们立刻抬起头。
然后天空中一架武装直升机已经变成了坠落的火雨。
而刚刚被它发射出的飞弹,因为失去了后面的引导,正在撞向地面的建筑。
很显然这架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很想进步,很想让老爷们看到他的英勇,结果应该可以得到老爷们的奖励。
只不过是刻在墓碑上的。
而那个金甲天使手持一张巨弓,正保持著拉弓姿態。
剩余几架武装直升机正在匆忙飞离,一架头脑清醒的甚至直接下降钻进了摩天大楼间。
金甲天使手中能量箭生成,瞬间化作蓝色流星飞出。
然后这蓝色流星正中一架逃离中的武装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爆炸中穿过火焰继续向前,又將前面另一架的尾部打掉,这才在空气中消散。
那架倒霉的武装直升机立刻转著圈坠落,紧接著在一座大楼上化作爆炸的火团。
下面那些士兵面面相覷,毫不犹豫地继续逃跑,甚至还有一辆坦克突然停下了。
然后它炮口下压,直接向对面射出炮弹。
一艘停在对面的豪华游艇上火焰炸开,洁白无瑕的身体就像被玷污一样瞬间黑了。
坦克里一片欢呼。
然后它那门主炮再次开火,另一艘游艇上同样火焰炸开,游艇主人原本还在举著望远镜欣赏,结果被爆炸直接掀飞。
这辆坦克就像打靶一样对著岸边那些停泊的豪华游艇不断点名。
而后面那些被夺取的战车开始向前,战车后面是汹涌的人潮,而逃离的队伍里又有两辆战车停下,它们很快和后面向前的匯合,最终两辆坦克,四辆步兵战车和多辆军车,在大桥上排成钢铁阵型向前。它们就这样带著人潮过了大桥,进入那片代表著財富的城区,而天空中杨丰依然在保护著他们,而这边的街道上一片混乱,部分跟隨过桥的开始砸开两旁商店甚至银行。
一家银行门前保安还举枪威胁,结果一辆步兵战车的炮塔转动,保安嚇得以最快速度扔了枪抱头蹲下。
那些狂欢的刁民们从他身旁蜂拥而入。
大堂经理还没反应过来,还愤怒的试图阻止,结果直接被撞倒然后被践踏而过。
刁民们和混在其中的几个士兵,快乐地冲向柜檯,在里面女职员们惊恐的尖叫中,一名士兵直接扛起火箭筒,紧接著火箭弹撞上防弹玻璃,爆炸中防弹玻璃化作碎片,然后端著枪的士兵冲了进去,后面刁民们蜂拥而入,火箭弹射手淡定的扔开发射筒,然后走到一名嚇傻了的顾客面前,从这个戴著名表的傢伙手中拿过手套箱。
后者还不鬆手。
他拔出手枪直接砸后者脑袋上。
这个明显拉丁裔的士兵感受著手套箱重量,满意的吹了吹口哨。
名表捂著流血的脑袋蹲在地上嚎著。
当然,这种事情杨丰是不会干涉的。
事实上这些人进入这片城区的主要目的应该就是这个。
这个国家持续多年的愚民化是非常成功的,底层熟悉的,也理解的,就是这种宣泄,而统治者们也喜欢这样,毕竟宣泄完之后该怎样还是怎样,但如果不让他们宣泄,那他们就要胡思乱想,一旦他们开始思考,那才是真正危险的。这种宣泄就像他们放开的那些东西,可以带来简单直接但短暂的快乐,然后在这种快乐中沉醉,不去思考那些对统治者来说可怕的东西。
所以之前睡王时候,他们寧可放任这种宣泄,甚至给予其一定范围內的合法性。
就是为了避免那些底层去思考啊。
当他们买不起商品就可以直接去零元购时候,他们也就不会想其他的,毕竟没有就去商店拿啊!
想那么多干什么?
至於损失……
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没有任何损失。
金钱对统治者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毕竟只是印刷机开动的那点成本,他们要的是控制,世世代代的控制。
至於那些老老实实开商店的,他们在统治者眼中,和那些直接去他们那里零元购的底层同样没有区別,甚至还不如那些零元购的,毕竟后者是真敢闹,而他们还在幻想著遵纪守法勤劳致富,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眼中这才是金字塔最底层。
有软肋啊!
杨丰也不是来带著这些人搞什么大事的,他就是扮演一个降临的天使,让这个天使成为这些底层幻想的符號。
他当然不是给他们带来公平社会的。
这个国家是否公平关他屁事,他就是个过路的,但是,他可以给他们带来公平的幻想,而这些就像洪水般涌入这片奢华的城区並向著一条条街道分流,然后砸开那些银行,奢侈品店,珠宝店的人,同样会成为这个国家其他城市里底层新的幻想。
可以学啊!
杨丰並不能带给他们改变,但当他们不满於现实的时候,就会渴望金色的天使降临。
他一个找乐子的路人,怎么可能管別的。
而此时这座城市的所有军队,都在向著这边增援,一辆辆原本等待阻击杨丰的坦克战车,从之前他们驻防位置撤出,然后来保护这片资本家云集之地。同样在这片城区,混乱也在迅速蔓延,狂欢的刁民们衝进一座座大楼,在里面洗劫能看到的財物,甚至衝进那些银行家的办公室,直接把他们扔出窗外。后者再也没有了当初围观占领运动的从容,被刁民们拖到他们当初观景的阳台,在他们的惊恐哀求中直接扔出去。
他们僱佣的私人武装已经保护不了他们,除了那些倒戈的士兵,刁民们也拿起了武器。
隨便找家枪店就能把自己武装起来。
事实上之前逃跑的那些士兵,这时候绝大多数也加入了抢掠的行列。
毕竟他们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世界各地都是烧杀抢掠习惯的,什么屠村,夜袭民宅残害小女孩之类都是经常乾的,本来就是一群贼配军,到那些被占领的国家烧杀抢掠,到了自己国家就变成好人了?匪过如篦,兵过如剃,贼配军都是这样,当国家有能力约束他们时候,只好老老实实忍著,但当秩序崩坏之后他们在自己国土上不会比在任何国家更文明。
自古秩序崩坏后,骄兵悍將才是最可怕的。
毕竟真烧杀抢掠起来,他们才是最强的,刁民最多拿著ar15衝进银行,他们却开著坦克衝进银行。
刁民打不开保险库,他们却可以直接上大炮。
至於被那些摄像头拍到又如何,只要抢的足够多,到拉美去换个生活环境很难吗?
而且这种情况还在迅速蔓延,那些保安很快也意识到自己还不如跟著干,而那些增援而来原本准备镇压的士兵,同样也突然发现与其和原本的同伴交火,还不如跟他们一样,看著他们手中那些装满金银珠宝的口袋,同样的贼配军们很难保持理智啊!
最先赶到的坦克上,那个站在机枪后的车长,看著对面一名佩戴同一个团袖標的士兵手中挥动的金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