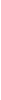这是平凡之人永远不会有的奇妙体验。
在那颗顏色猩红,质地软弹的“辽丹”从路明非的口腔进入胃部之后,好像並没有被胃袋兜住,它继续的下坠,下坠,直至化为一抹微不可查的红光,坠入一片漆黑的深渊。
但路明非的身下怎么会有一片看不见底的深渊呢?他刚刚不是盘坐在“冰窖”底层的青铜地面上么?
原来如此,路明非忽然明白了。
那不是“辽丹”的下坠,而是他的“上升”。
他正在从一片模糊漆黑的深渊中上升,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到什么地方。
亦或者他其实是在下降,“辽丹”在上升?
纠结於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於来到这片模糊深渊的路明非来说,空间与方向已经失去了意义。
与之类似的还有时间感,路明非觉得仿佛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又好像只是短短一瞬,意识转动的下一个瞬间,他就从那仿佛没有尽头的模糊深渊中脱离了出来。
仍旧是没有光存在的空间,但路明非却能看到,他的身躯已经被“角度”与“弧度”包围了,眼角的余光里,一幅幅杂乱的画面正在不停的闪动。
他本能的尝试著將注意力放在那些杂乱的画面上。
第一次的尝试並不顺利,由於那些纷乱的画面闪动的速度实在太快,路明非只能看见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图画。
被群山与红色枫叶林之间,蚂蚁大小的黑点来回穿行,铁轨与卡塞尔学院平地而起:
一群穿著皮靴与红色猎手服的白人坐著巨大的蒸汽船而来,他们长著棕红色与金色的头髮,端著燧发枪,追逐头戴羽毛,脸上抹著油彩的印第安人;
带著镶嵌著宝石的古老面具的野人,颂念著奇怪的咒语,將五顏六色的顏料涂抹在灰黄色的石壁上,绘製成一幅幅抽象的壁画,面具孔洞中金色的瞳孔比面具上镶嵌的宝石还要闪耀这是·这片区域曾经的歷史?
“辽丹”已经开始生效了?
路明非不由自主的侧过头,想將刚刚余光中的图景看得更清楚一些,但隨著他头颅的转动,原本还算勉强可以看清的图像之间变成了一大块模糊的光晕。
等到光晕平息,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华美,金碧辉煌的宫殿,雕刻著龙形浮雕的青铜立柱与散发著奇异香味的宫灯在大殿两侧对称布设,大殿深处,宫灯光焰照不进的地方一片可怖的黑暗,穿著宽袍大袖,带著头冠,手执笏板的官员与在大殿的两侧侍立而站。
一个服饰明显有异於其他官员的冷酷精瘦男子,手捧著一个绣著精美浮雕的捲轴,带著一个面容惊恐而身材强壮的侍从从殿外缓步走入殿中。
他一步一步的越过两侧的官员,走到大殿的尽头。
他的身影还没有消失多久,一声让人肝胆俱裂的恐怖龙吟声就从那片黑暗中爆发了出来,而后一条身形巨大的黑龙从黑暗中飞了出来,盘绕在殿中的青铜立柱上。
面容冷酷的精瘦男子手持一柄造型古朴的短剑,从黑暗中追了出来,他仰头看著盘绕在青铜立柱上的巨大黑龙,表情变得极度难看。
下一刻,黑龙张开嘴,炽热的龙焰从他的喉咙中喷吐出来,冷酷男子的身影在金色的火焰中痛苦的扭动,挣扎,最后一动不动。
他死了。
看了一场好戏的路明非愣了愣。
“荆軻刺秦王”。
他在昂热校长的“龙族谱系学”中看到过这个案例,说歷史上荆軻的言灵是刺客型的言灵,能力是可以以鬼魅般的速度出现在敌人背后。
他带著抹著致命链金毒素的链金刀剑“鱼肠”,想凭藉著言灵与毒素去刺杀始皇帝,结果始皇帝现出真身,整个龙躯盘绕在青铜立柱上,藉此就抹除了“后背”这个概念,转头反杀了荆軻。
只是转转头,观测地点就从北美挪移到中国了?幅度这么大么?
那时间点呢?是根据什么而变化的?
路明非一时间摸不清“辽丹”的规律,他的好奇只是浮现了短短一刻就被他掐灭了,他小心翼翼的控制自己的头颅挪回原处,精神放空,不再留意余光中那些闪动著的画面。
路明非的心中其实存留著许多疑问,比如说在暑假返乡后对他处处针对的幕后之人,阿撒托斯请神是否已经泄露等,但他还是强行压制了“观测时间线”的衝动。
服用“辽丹”后放纵探索欲,到处乱跑容易吸引到廷达罗斯猎犬的注意,是大忌中的大忌。
他只是在这片虚无之地静静的等待。
等待现实中正在进行的“仪式”完成。
“该死的,混,混蛋—””
被禁的看守学员发出像是诅咒,又像是呻吟的微弱声音。
隨著时间的推移,“冰窖”底层刚刚被路明非隨手扭曲的空间正在缓慢的復原,他的眼珠也因此可以略微的移动了。
他感觉得到他马上就要死了,但他对这一切的发生与进行却仍然一无所知,一股强烈的悲哀从他的胃部涌起,让觉得嘴里里一阵泛酸。
他用尽全力转动眼球,视野偏移到斜前方,偏移到盘坐著背对他的“路明非”身上。
那个从未见过的,恐怖的怪物到底在干什么?
他想要干什么?
猩红的血液在“冰窖”底层的地面上流了一地,与他共同看守龙王的三个死去的同学已经全都不见踪影。
“路明非”的背影从背后看上去有些消瘦,他姿態放鬆,像是睡著了似的,头深深的垂下,让人不由得担心他会不会直接栽倒到地上。
由於两张血肉符篆被摆放在“路明非”的身前,在他背后的看守学员的视野里只能看见一阵淡蓝色的烟雾从“路明非”前方升腾。
在蓝色的烟雾逐渐消散之后,一股难以形容的臭味与轻微的响动,出现在几乎与外界隔间的“冰窖”底层。
不知为何,被扭曲的空间禁著的看守学员心里莫名其妙的萌生了一个想法:
不是求援了却迟迟没有出现的校长,而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要来了。
看守学员当即就抹掉了直觉中诞生的这个荒诞想法,有什么东西能跨越地面上的冲冲阻碍,进入“冰窖”的底层呢?
这压根是无稽之谈。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说好的“龙王”会变成这样的怪物,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怪物现在被困在“冰窖”底层无法离开,这代表著他迟早会被地上学院里的人抹杀。
这就够了。
刚刚受伤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已经消散了,看守学员只觉得自已折断的左腿撕心裂肺的疼痛,他的额头因此冒出一层冷汗,顺著眉骨流下,流入他血丝密布的眼晴里。
他无法控制眼皮移动,只能用力晃了晃眼球,希望能把蛰得他眼睛生疼的汗液排挤出去,但这个动作除了把他眼球上的汗水涂抹均匀,让他几乎无法视物之外,再没起到其他的作用。
看守学员感觉自己像是带了一个度数极高的近视镜,又像是在眼前放了一块毛玻璃,“路明非”消瘦的背影只剩下五顏六色的一团模糊之物。
错觉么?看守学员觉得刚刚就已经出现的臭味好像变得更难以忍受了一些,而那轻微声响似乎也变得更清晰了一些这声音中的饥渴与恶意浓烈得无可言状,它们似乎从四面八方而来,充塞了原本还算宽的“冰窖”底层,听起来像是犬吠?
看守学员在心里暗暗自嘲。
怎么会有犬吠?怎么会像犬吠?
难不成是他已经疼的出现幻觉了?
等等,前面那是什么?
在“冰窖”底层青黑色的背景中,路明非那团模糊消瘦的一团,身边好像出现了几团细长的深黑色之物。
那是什么啊.—
明明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但看守学员似乎感受到了那细长的深黑色之物身上匯集了令人抓狂的浓烈恶意。
他本能的想要尖叫著逃离,但却被禁在扭曲空间,身上能动所有部位都拼命的剧烈颤抖起来但那几团细长的深黑色之物並没有理会惊恐的他,它们环绕著“路明非”那五顏六色的一团转了转,隨后,伴著恐怖的啃食之声,“细长的深黑色之物”开始侵袭“五顏六色”的一团。
它们,它们在“吃”那个怪物。
是不是吃完那个怪物,就要轮到他了?
毫无疑问,极度的恐惧已经完全占据了这个可怜人的心神,明明他刚刚已经心怀死志,要跟怪物同归於尽,此刻却觉得经歷的每一秒钟都像是被千刀万剐似的无法忍受。
他就这样度秒如年的挣扎,挣扎,不知何时,空间的扭曲已经被抚平到容许他做出“眨眼”动作的程度了。
汗液隨著他不断眨眼被他从眼眶里排出了一些,视野也因此变得清晰了一些。
他的眼晴猛的瞪大,而后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这—
那几团细长的深黑色之物仿佛是一场骇人的噩梦,此刻已经消失不见,只有那个背对著他盘坐的怪物像是被撕碎的布娃娃似的,只剩下了几块残破的碎片,淡蓝色的黏液洒得到处都是。
怪物——死了?
而他,活下来了?
这是一场梦吗?
原本禁著看守学员,让他连转动眼球都做不到的力量也在不断的消退。
从眼球,再到眼皮,再到可以晃动手指,大约十几分钟之后,空间的扭曲被抚平,他从半空中跌落,摔到地上。
折断的左腿虽然没直接砸在地面上,但身体与地面相撞產生的剧烈震动还是让看守学员疼的眼前一黑。
他狠狠喘了几口粗气,过了大概十多秒才从那阵难以忍受的疼痛中清醒过来,真的结束了?
看守学员感觉一直蒙绕在“冰窖”里那股令人室息的恶意消退了,久违的轻鬆感让他头脑发晕,暂时忘却死去的同伴和折断的左腿,他微微张嘴,发出微不可闻的笑声。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看守学员忽然问道。
“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
看守学员不加思索的用带著哭腔的兴奋声音回应,回应回应谁?
是谁在跟他说话?
恐惧像一颗炸弹似的在他的胸腔引爆,他顿时感觉呼吸困难,面色涨红,身体开始剧烈的抽搐起来。
可是,无论身体怎么抽搐,他的面容依旧温和平静,只是嘴角含笑,点了点头:
“能在这么危险的事件中活下来確实不容易,恭喜你。”
接著,怪物尸体的碎块中,有一枚比黄豆大了一些的,猩红色的丹丸漂浮出来,在链金法阵深槽里生青色的水的映衬下,似乎能看见丹丸上漂浮著一个单薄消瘦的,雾气一般的身影。
“不.—.不!”
看守学员双手撑地,飞快的像后方挪动,他的腿部正在剧烈的发痒,露在外面的鲜红血肉与森白的骨骼正在时光倒流般的快速修復。
下一刻,他惊恐扭曲的脸忽然又像是精神分裂了似的,重新变得古井无波:
“你连要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坚强点。”
看守学员的眼睛瞪大,绝望的看著那枚猩红色的丹丸飘入了他的口腔,顺著食道向下坠落,最终隱入了一片无形之处。
“『b』”级学员柯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龙王在『冰窖”底层链金法阵的压制下甦醒了过来,並且对你们发动了偷袭?”
“你们由於也被链金法阵影响,没能第一时间发动言灵反击,虽然最后依然击败了龙王,但是死伤惨重?!”
“最终只有你一人倖存?!”
奥丁广场上,早早就掉光了头髮的风纪委员曼施坦因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走动,他的表情沉痛,夹杂著浓浓的不可置信,“这,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现在就联繫校长!柯晨同学,你真的確定吗?!”
在“冰窖”底层昏暗闭塞的环境里呆习惯后,忽然被清晨温暖和熙的阳光洒在身上,让路明非略微有些不適应。
他本能的將手放在眼前遮了遮照在脸上的阳光,嘴角勾起:
“是的,我確认。”